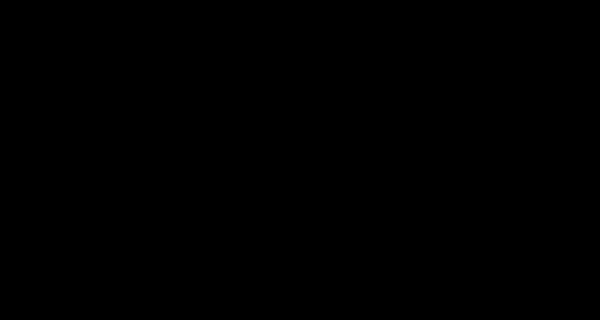倫敦是無數音樂風格的發源地。Broken Beat、Jungle、Dubstep 和Grime等在地音樂運動,各自承襲了先前的風格和文化,也啟發了全球各地的音樂人。
這些音樂場景大多出現在城市邊緣地帶,租金較便宜,空間的取得也稍微容易一些。能夠身處一個激盪出全新聲音的城市,是音樂人選擇倫敦作為基地的原因之一。而在追求新事物的地方,事情的發展可以很快。
Audrey Powne:「電台力挺獨立音樂」
Audrey Powne是一位來自墨爾本的小號手、歌手和製作人, 2024年1月搬到倫敦,部分原因就是受到國際知名爵士音樂運動的啟發。Powne表示:「難以否認,倫敦的音樂場景正在製作著全世界最獨特且令人興奮的音樂。源自倫敦各種流派的原創音樂,它們的多樣性和產量都不容小覷。」
然而,最近這座城市發生一連串的變化。脫歐、疫情後的環境使生活成本成為一項危機。今年夏天,工黨壓倒性贏得了大選, 擊敗執政14年的保守黨政府——一個通常不受藝術界人士歡迎的政黨。不久之後,英國極右派卻在全國,包括首都煽動了多起種族暴動——即使挺身保護鄰里的反種族主義者人數遠遠超過了他們。
儘管危機四伏,倫敦人依然積極為社區發聲:每個週末的地鐵上都可能看到一片片的標語,當地人手握標牌,為戰爭、氣候變遷、格倫費爾火災(Grenfell Tower tragedy)等議題發聲。
這樣的社區意識也一直反映在倫敦的音樂場景中,而在動蕩的時代,在地的音樂場景更是為音樂人和聽眾提供了聊以慰藉的安全空間。
倫敦的獨立廣播電台,如Rinse FM、Voices和Soho Radio,以及國際知名的NTS和Worldwide FM,為大多數獨立音樂人提供關注和言論的自由。只要花一些時間沉浸在倫敦的音樂場景中,不難發現,無論是音樂人和主持人的電台採訪過程,或是現場表演的音樂人和觀眾之間,都充滿建立友誼的契機。
同時,大多數唱片行和唱片公司都願意與音樂人直接交流。正是音樂人和愛好音樂的相關專業人員(如公關、節目策劃、廣播員和唱片公司負責人)之間即時、親密的關係,使倫敦讓遠道而來的音樂人感到如此友好。

來自墨爾本的歌手Audrey Powne,同時也是一位小號手和製作人。Photo Credit: Anna Francesca Jennings
Powne的經歷說明這樣的潛力對生活帶來的巨大影響:「當初搬來倫敦的重要催化劑,是和位於 Hackney的傳奇獨立唱片公司BBE簽約。」
「我直接發了一封電子郵件給他們,唱片公司創始人Pete Adarkwah在24小時內親自回覆,我們在48小時內就開始討論專輯。我簡直不敢相信正在與操刀J Dilla第一張專輯和Brian Jackson最新專輯的唱片公司進行認真的討論。對我來說,在墨爾本,光是地理位置就無法實現這種聯繫和機會。」
搬家六個月後,Powne回顧了她對新家的第一印象:「我對音樂界的支持和大家的正向能量感到驚訝——尤其是我所處的小型爵士與靈魂音樂社群,好多事情正在發生。不僅有這麼多令人興奮的音樂人和藝術家努力製作原創音樂,Jazz re:freshed、NTS、Soho Radio、Worldwide FM甚至BBC 等平台都為年輕藝術家提供展現專業技藝的機會。」
「這裡的音樂家有一種特殊的能量,受到非洲和加勒比海移民,加上英國俱樂部文化的影響,它以專屬於倫敦的方式不斷為音樂注入活力。」
倫敦因多元的文化而聞名,街道上到處都是加勒比海餐館、土耳其理髮廳、日本糕點店和具有各種文化特色的社區中心。正是這種多樣性組成了這座城市的聲音,音樂家們得以結識同樣離鄉背井的創意夥伴。也許這就是為什麼倫敦的音樂界總是走在潮流前方。
身處地下音樂場景的藝術家,通常特別了解文化、社會和政治問題,很少錯過參與社區行動的機會。藝術家們聚集在每週的即興演奏會,像是Steam Down和Orii,朗誦或演唱剛寫好的詩歌,並在民間贊助者組織的獨立活動中會面。無論是在Buttmitzvah尋找酷兒、猶太夜生活,還是在Dialled In活動中享受南亞音樂和文化,任何社群都受到歡迎。
同時,諾丁丘嘉年華(Notting Hill Carnival)、BBC逍遙音樂會(BBC Proms)等眾多節目,從拉丁音樂的La Linea到LGBTQIA+族群領導的Mighty Hoopla年度活動,也都提供了源源不絕的機會。
有一部分得歸功於倫敦豐富的文化和多樣性,這座城市的音樂創意人持續證明自己的韌性和敏捷。然而,儘管居住在倫敦一直都十分昂貴,生活成本上升造成的危機自2021年以來不斷惡化,導致藝術家的生活條件變得更加艱難。

來自委內瑞拉的鼓手Lya Reis Guerrero。
Lya Reis Guerrero:參與Poppy Ajudha的巡演
由英國組織Help Musicians和Musicians' Union領導,有史以來第一次音樂家普查於2023年9月發布。結果令人擔憂:在英國從事音樂工作的平均年收入為 20,700 英鎊,遠低於全國平均水準 34,963 英鎊。更嚴重的是,43%的音樂家每年從音樂中獲得的收入不到 14,000 英鎊。
「如果你在一個大機構的商業樂隊裡演出,也許可以有一份不錯的收入——但這對創作來說並不具吸引力,」已在英國生活14年的鼓手Lya Reis Guerrero說。
「不幸的是,我搬到倫敦是因為委內瑞拉當時太危險了。儘管在那裡的音樂事業很成功,但我不得不前往其他地方發展。」
「我不知道怎麼靠音樂過上體面的生活,不得不開始在酒吧和咖啡館工作,直到找到一份與本業相關的工作——音響工程。它讓我能夠支付帳單,同時在音樂圈打出名氣。」
如今,她與COLLECTIVA合作演出,並成為歌手Poppy Ajudha演出的班底 。

義大利音樂人Sans Soucis到倫敦發展,並被迪卡唱片(Decca Records)簽下。Photo Credit: Elijah Craig
Sans Soucis:從義大利搬到倫敦的音樂人
Sans Soucis 是一位非二元性別的義大利、剛果混血音樂人,十年前從義大利搬到倫敦。「老實說,倫敦不是我的首選!我當時與這裡的文化完全沒有共鳴,身處英國以外的年輕人,對倫敦的印象只有女王、白金漢宮(Buckingham Palace)和倫敦眼!」
我當時想:「那不是屬於我的地方——我想去美國。倫敦是『B 計劃』,但在這座城市生活了十年,並通過迪卡唱片(Decca Records)發行首張專輯時,便不再感到懊悔。」
「我在倫敦發現了好多音樂。來到這裡時,我就想:『我之前去哪兒了?』就音樂的品質而言,這是我在世界上最喜歡的城市。但以這座城市的整體現況,我還是不會推薦搬過來⋯⋯我現在開始用不同的方式思考資本主義如何塑造我們的職業和願景。這是一個非常昂貴的城市。」
在倫敦生活的成本無可迴避——它在美世諮詢(Mercer)的2024年世界城市生活成本調查排名第八——但在這裡,音樂界對社區的支持再次展現出來:英國的音樂組織努力在可能的情況下支持音樂人,提供資金和發展機會。
PRS基金會同時為新銳和成名音樂人提供多種資助,包括PPL Momentum Fund、Women Make Music和International Showcase Fund。Little Simz、Sam Fender和Young Fathers都曾獲得組織的贊助。
與此同時,康登鎮傳奇的Roundhouse場地為25歲以下的青年族群舉辦大量活動,例如低至2英鎊門票的製作人交流會。前面提過的Help Musicians在通過申請門檻後,更提供高達3000英鎊的經濟支援。
不要誤會,如果沒有運氣,也不熟悉這座城市的資源,那麼在倫敦成為一名音樂人的現實——就像在任何大城市一樣——就是一場艱苦的奮鬥。理想上也許是浪漫的,但實際上,就是放手一搏。 並非每個人都能得到這座城市的鑰匙。
不過在這裡,夢想確實可以實現。某種程度上,在倫敦甚至可能比其他地方更容易得到資助:這裡有大量的獨立和主流廠牌,無論白天或晚上都有演出和曝光機會,這是一個緊緊關注潮流引領者的音樂文化。
儘管搬到倫敦的音樂人必須面對許多挑戰——也同時享有相應的回報——有一個問題他們可能永遠無法克服:這裡的天氣。